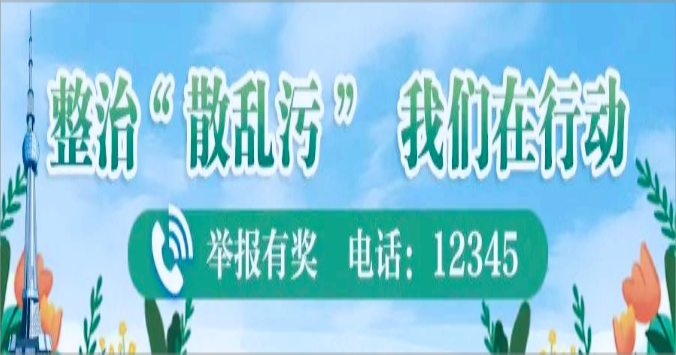来源:学习强国
来源:学习强国
 添加时间:
2024-10-15 08:23:43
添加时间:
2024-10-15 08:23:43
 阅读量:
阅读量:

1964年,刘慎谔骑着毛驴在西北检查治沙试验工作。

1981年,曹新孙(右二)陪同瑞士林学家波斯哈特(左三)到带岭工作站考察。

2018年,朱教君(右二)考察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研究站固沙植被。

防护林的3种主要林型之水源涵养林

防护林的3种主要林型之防风固沙林

防护林的3种主要林型之农田防护林
曹新孙根据自身实践编著的《农田防护林学》,其初稿曾在1979年至1980年印刷成册,作为他授课的林业部三北工程(防护林)营造技术讲习班教材,分发给广大基层林业技术骨干,成为人手必备的入门教科书。
“当时大家只知道要造林,但普遍缺乏技术,这本书为三北工程一期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朱教君说。
后来,农田防护林研究获得第三世界科学组织网络奖,表明国际社会对该研究的认可。激动之余,姜凤岐在日记里写下一首小诗:“常言要为国争光,多年夙愿今日遂。前路峰高更待攀,相期口碑胜金杯!”
三代接力与三北工程共成长
1986年,三北工程进入二期工程阶段。此时,工程建设的目标发生了变化。
“一期工程主要是把树栽活,属于造林范畴,二期工程则涉及经营管理问题。”朱教君告知,所谓“造林一时、经营一世”,如何经营防护林是一门更大的学问。
但防护林不同于普通森林,不能仅仅考虑木材产出,更重要的是取得生态防护效益。加上三北地区严苛的自然环境,原有的森林经营理论基础已经无法支撑。
为此,姜凤岐连续主持国家“七五”“八五”“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历时15年专攻防护林经营研究。为了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他多次带领团队深入实地进行区域性考察,与多部门协作设置了百余项试验,并建立了大量试验示范林。
凝结着大家心血的《防护林经营学》于2003年正式出版。该书将防护林经营在学科层面加以系统提炼总结,成为该领域又一本重要的教科书。“北方防护林经营理论、技术与应用”获得了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7年,三北工程即将迎来40周年之际,姜凤岐再次回到辽宁省昌图县试验基地。看着自己当年栽植的油松林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已成为一道道“绿色长城”,他不由感叹:“此生足矣!”
进入21世纪,国家对防护林建设的需求更加注重从生态学视角进行系统治理。此时,学科带头人的接力棒交到了朱教君手中。一直跟随姜凤岐从事防护林学研究的他,在2023年主笔完成了《防护林生态学》。该书成为新时代防护林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教科书,入选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教材。
朱教君表示,防护林生态学的终极目标,是将防护林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有机结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经济“双赢”发展模式。
“例如,我们研发了林药、林菜、林蛙复合经营范式,在大幅提升防护功能的同时,促进了林区产业发展。”朱教君说,经过这样的改造,森林水源涵养与固碳等生态功能大幅提高的同时,林下道地药材、山野菜和林蛙等产量也提高了20%至30%,在3年内帮助5.1万名林农脱贫——同时收获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据悉,三北工程带动了林下经济、特色林果业等发展壮大,为全国提供了1/4的干鲜果品,助力1500万人脱贫增收。
从1983年到2003年,再到2023年,三代学人分别用20年时间赓续传承,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防护林生态工程建设的需求,接力走出一条科学探索之路。
科学护航打好三北攻坚战
40多年来,三北工程的正面效益有目共睹。以世界上第一个即将消失的沙漠——毛乌素沙漠为例,1984年的卫星影像几乎全是贫瘠荒芜的沙化土地,如今80%的面积已经成为绿洲。4.22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就这样被中国人通过种树“消灭”了。
为了客观、准确地评价三北工程,中国科学院在2008年和2018年——三北工程启动30周年、40周年之际,开展了两次综合评估。
尤其是40周年这次评估,更像是对三北工程的一次“期中考试”。受国家林草局委托,朱教君团队耗时数年,在三北地区行程7万公里,获得大量一手资料;收集整理了23万余个涉林样地的定位观测、监测和调查数据,分析了1978年以来近2000景遥感影像,对三北工程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
2018年12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发布《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40年综合评价报告》,郑重宣告,三北工程实施40年来,累计完成造林面积4614万公顷,占规划造林任务的118%;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净提高5.29个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相对减少67%。
这是40岁的三北工程向全国人民交上的一份答卷。它的背后,离不开科研工作者不断升级的科技手段。
上世纪90年代初,最早引种到科尔沁沙地东南缘的樟子松固沙林发生大面积衰退现象。朱教君团队通过实地调研、野外试验,采用同位素示踪、探地雷达等新技术进行分析,指出衰退是由于农田过度开垦导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而樟子松为浅根系树种所致。此后,他们提出以区域“全量水资源”平衡为依据的综合生态系统一体化构建方案。
为了对三北工程进行长期持续的碳汇监测,沈阳生态所设计建成了全球首个森林科研大装置——清原-科尔塔群,配套了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数据信息系统,以及基于人工智能分析计算的数据中心,大幅提升了监测精度。据测算,清原—科尔塔群监测的三北工程项目区内,现有森林每年每公顷固碳量接近2吨。
“这些事说起来简单,但一做就是30年,其实也不简单。”朱教君笑着说。
此外,朱教君对大装置还有一点“私心”:通过变革科研范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林学、生态学研究队伍,为三北工程储备后续力量。
“80后”研究员郝广友刚加入沈阳生态所时,朱教君就鼓励他到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的大青沟沙地生态实验站开展一线调查和研究。当地条件虽然简陋,但郝广友说:“这里对我们开展科学研究来说是个很理想的地方。”
如今,三北工程已进入第六期建设。针对北方区域生态环境依然脆弱的问题,党中央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
如何打好这场攻坚战?
“一是让应该有且能够有植被保护的地方,都有林草;二是对已有林草植被但出现衰退的地方,进行科学修复、改造;三是在植被构建存在困难的地方,通过科技创新攻坚克难,使林草植被尽快构建起来。一句话概括,就是打造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统筹发展的实践样板。”朱教君表示,同40年前相比,现在要更加尊重科学规律、重新向大自然学习,让祖国的“绿色长城”屹立不倒。(陈欢欢 沈阳生态所供图)